摘要:乡土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临危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精神返乡”模式遭遇困境。美籍华裔作家蔡铮的乡土叙事极为自觉地摒弃了传统乡土文学的“怀乡病”情结,其以内在视角对乡土社会困境的呈显,在当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关键词:乡土叙事;内在视角;怀乡病;蔡铮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1-0068-05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脉主色,乡土文学几乎完整贯穿了“五四”、“京派”、“左翼”、“十七年”、“寻根”、“新写实”等等思潮和时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乡土题材文学创作的繁荣,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瞩目的事实。只要我们稍稍留心一下,便不难发现,在整个现代文学作家队伍中,无论是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还是剧作家,创作不涉足乡土题材的很少。”①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乡土社会的急剧转型、乡土人的大规模流动、文学创作者和阅读者的代际更替等诸多因素,乡土经验受到城市经验强有力的渗透和冲击,乡土文学也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关于乡土文学“危机”、“终结”、“重新开启”的讨论甚多并持续至今。如何重新审视乡土文学,进一步开掘乡土叙事的空间?这是当下有待思考的一个问题。美籍华裔作家蔡铮②的小说集《种子》,收录了他从1988年到2011年创作的15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有6篇曾先后发表于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从故事的题材(乡土生活)、背景(农村)、人物(农民)来看,《种子》无疑是传统乡土文学的延续。然而,蔡铮笔下的“乡”与“土”实际上又是一片荒芜可怖的“异乡”“弃土”:既无法寄托“乡恋”,也难以安放“乡愁”。这使其与传统乡土文学中常见的“怀乡病”情结和“精神返乡”姿态拉开距离。对此个案进行透视,对当前关于乡土文学的讨论或具一定启发。
一
从题材角度来界定乡土文学,并总结出诸如“风土人情”、“地方色彩”、“异域情调”、“风俗画”、“农村农民”等内涵和特质,这已为许多作家和文学研究者所接受。由此思路展开,“乡土社会”的深刻转型和“乡土生活”的日趋瓦解,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乡土文学”的危机甚至终结。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乡土”远不止于一个题材概念,更是一个承载和建构审美想象、思想话语的重要场域。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批判中,“鲁镇”和“乡土人”是“旧中国”与“国民性”的表征,是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并亟待拯救的愚昧落后之地。在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为代表的诗意想象中,“乡土”成为与城市文明和政治话语分庭抗礼的桃源异乡。在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那里,“乡土”是以阶级性、民族性建构*的重要资源。在改革开放以后“知青”一代的乡土叙事中,“乡土”担负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文化民族性的反思、认同甚至重塑。③多数情况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乡土”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也是一个心理-文化概念,是作?“家园”、“故土”、“国家”、“大地”、“传统”、“人民”、“生命力”、“理想”、“希望”等等意义维度和价值维度的承载者。作为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国家,乡土经验不仅深刻渗透于那些成长于“乡村”“土地”且在后来进入城市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也深刻渗透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甚至集体无意识。就此而言,中国城市空间及由之承载的现代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乡土”的延伸。这正是“乡土”与“中国”得以互构并成为“意义负载物”的深刻背景。在文学现代性叙事和想象中,“乡土”与“城市”、“工业”、“文明”等等“现代性”因素的相互遭遇、激烈碰撞,在一定程度上恰凸显出作家自身乃至知识人群体心理-文化体验的内在复杂性。正因为此,它才成为启蒙主体、抒情主体、革命主体和文化寻根主体不断进行“投射”的理想空间,成为漂泊游荡的现代知识心灵念兹在兹的怀想之所、苦恼之源、寄托之地。一句话,乡土文学的长久繁盛和广泛影响,恰恰彰显出现代知识人所常见的“精神返乡”情结。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土文学面临的所谓“危机”首先还不是现实“乡土”的剧烈变动,而是“精神返乡”情结和由此展开的乡土叙事模式在新的背景下变得不合时宜。首先,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真实的乡土几乎总是作为工业积累的原始供给、城市危机的缓冲地带、舆论议程的遗忘之地而存在。虽然一度被各种政治话语、文学话语频繁代言,但真实的乡土却常常失语,用陈晓明教授的话说,它是一种“不具有语言表达的历史客体”。④随着进入城市的“乡土人”特别是年青一代逐渐习惯借助网络和自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打工文学”、“打工诗歌”在主流文学权力体制之外开辟出自己的言说空间,曾经的“被投射对象”已经开始具有自行言说的能力??尽管目前还十分有限。可以想见:当身在城市的知识人不断从“乡土”中开掘出诸如“童年回忆”、“淳朴民风”、“田园风光”、“自然活力”等等面向以作为寄托个人怀想的杳远之地时,真实的乡土人却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不断端呈出真实乡土的落后、破败、空心化。两者之间不断加大的空隙只会加剧传统精英文学“代言”结构的进一步失落。其次,只要城乡资源分配结构没有在根本上得以改变,亿万乡土人“背乡”“离土”“拔根”“进城”以及乡土社会日趋衰弱的整体趋势就难以扭转。在工作、户籍、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老人赡养等现实问题面前,“乡恋”、“乡愁”无疑是一种也许偷藏于心却又过于奢侈的情绪。在市场经济理性和消费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在无“乡”可依、无“土”可返、漂泊孤立的现代体验中,传统乡土文学“寻找家园”“落叶归根”“返回源头”的意义冲动不再一如往常那样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正如丁帆教授所指出: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界都弥漫着一种“逃离家园”、“逃离故乡”的情绪。⑤面对剧烈变动的现实经验,精神、文化层面的所谓“怀乡情结”越来越像是一种“怀乡病(homesickness)”。
处身于这样一种背景下,乡土叙事又将沿何种路向拓展其可能空间?作为一位经历“80年代”洗礼和“90年代”转型的作家,特别是作为一位长期定居海外的华文作家,蔡铮当然也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时代情绪。但与当时“寻根”热及之后一些乡土叙事中仍潜存的“寻根”情结、“诗化”情结不同的是:他返回到乡土文学发生伊始的源点??对乡土社会内生困境的观照。
二
在“皇权不下县”、“国法不下乡”的传统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基础上世代累积而成的生活经验、伦理风俗、乡规民约,一直是维系“世道人心”的基本资源。然而,在由“传统”向“现代”的激烈转型中,“外部”因素、“上位”(国家政权)因素不断向“基层”渗透,并在权力配置、阶层划分、行为规范、价值理念等方方面面对其进行冲击和重构。《种子》中的15个中短篇几乎串联起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中国乡土社会近百年的历程。百余年来的政权更迭、社会治乱、战争运动、市场经济、城乡融合等等因素,都作为雌伏的故事背景发挥着作用。但是,《种子》的侧重点不在于“外部”对“内部”的渗透、冲击、干预,而是乡土社会的“内部”困境及其所造成的创伤。鲁迅、彭家煌、王鲁彦、叶绍钧、许钦文、台静农、赛先艾、许杰等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创作的早期乡土文学作品中,对于礼教、饥荒、苛税、节烈、愚孝、陋俗、家族矛盾、乡间械斗等等乡土社会内生问题的揭露和反思有其深厚传统。《种子》无疑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有所不同的是,蔡铮几乎悬置了早期乡土文学中基于现代启蒙立场的各种“外部”参照和视角,而是展示乡土社会“内部”本有的伦理规范和价值逻辑如何遭遇困境,进而一步步走向衰败和解体。这使他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都几乎带有“伦理实验”的意味。
《种子》涉及最多的就是“吃”。蔡铮笔下的乡土角色,外出当兵是为了“一日三餐是管饱”(《最好的菜》),读书识字是为了“换一大海碗干饭”(《读书》),家庭纷争、父子矛盾是因争夺吃食而起(《油条》),甚至连时间长短都要以诸如“喝几碗粥的功夫”来表达……“吃”,不仅是维系个体、延续家族的必需,也是组建农耕劳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目标。然而,乡土经济“靠天吃饭”的固有封闭性和脆弱性,使其极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而沦于饥饿的边缘。正因为此,饥恶体验始终贯穿于《种子》的多篇小说之中。《狼猪》就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强炎畜养的家猪本是用来吃或卖,可它却因饥饿产生了嗜血食肉的狼性,最终吃掉自己的孩子。叙述在故事世界和强炎梦境两个层次之间不断滑动:“狼猪”既像是故事世界里真实发生的变异,又像是强炎梦魇中的恐怖意象外化到真实生活之中,它也许就是饥恶体验在故事角色甚至作者本人那里积累而成的创伤。
对乡村而言,在份量上堪与“吃”相当的另一主题则是“生育”,然而不育也成为这片弃土上挥之不去的梦魇。《种子》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盛福夫妇一直没有小孩,算命先生说这是报应,因为他曾“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找到自己害过的人来补救;要么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罪行来免过。盛福一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坏事就是在十七八岁时将霉变的种子卖给一个河南人。他为此到处寻找那人而不得,最后夫妻俩在悲哀绝望中死去。《贵花》则展示出更为深层的绝望:在那个饿殍遍地的时代,不孕的希才收养了另一家准备杀掉的女婴贵花,希望用自己家唯一一只鸡下的蛋来给可怜的孩子提供营养。然而,那只鸡不仅没有下蛋,反而趁主人不留神时一口吞掉已经瘦得蝉蛹般大小的婴儿。
家庭关系是维系乡村共同体的血缘纽带,也是奠基乡土伦理的情感基础。但在蔡铮笔下,温情的亲伦之下时可窥见野蛮粗鄙的权力。其中,不同故事里的“父亲”形象构成一组意味复杂的人物系列。在《油条》中,父亲“用老婆刚卖了鸡蛋的钱”买了两根油条用来压药,儿子看着油条仅仅流了几下口水,就被父亲一顿臭骂。儿子“从未见过鬼,猜想鬼大概就是父亲这个样子吧:两眼凶狠,嘴很尖。”在《六根指头》中,全家最好的吃食都让父亲吃了,只要孩子们闻着香味过去张看,“父亲总瞪着一双绿眼恶狠狠地横着他们”。甚至姐姐在一年级时获得的奖状也被父亲毫不顾忌撕成两半用来卷旱烟。在《走》中,儿子亲眼看到了作为村干部的父亲背着母亲和别的女人在野地里偷情,亲眼看到父亲吊打无辜的“老地主”最后逼得别人家破人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父亲”,既是“旧社会”父权制的代表,也是“新社会”家长威权的象征,他通过压制、蛮横、掠夺甚至厚颜无耻来维护家庭关系及其延伸物的稳定,而这种稳定之下所掩盖和压制的怨恨又成为父权统治的危机。笼罩于“父亲”阴影下的“儿子”们无疑是复杂的。一方面,外在的父权已经渗透和内化到“儿子”的心理和生理之中。正如《油条》中的小男孩在油条被猫偷吃之后,怕父亲第二天迁怒于自己,绝望地以父亲的口吻来不断地自己教训自己。父亲显然已经成为其“超我”的一部分。而在《六根指头》中,父亲已经“长”成儿子自己的大拇指,只要举起自己的大拇指,似乎就像看到自己的父亲。但是,另一方面,“儿子”们也在不断尝试对“父亲”进行反抗、斗争甚至决裂。正如《六根指头》中的儿子“常用牙咬右手上的大姆指,用瓦片刮它,用长着厚茧的脚跟踩它,用刺锥它,把它放在门前又粗又糙的石头上磨,有时弄得大姆指冒血,痛得直流泪。好几回他拿了菜刀,把姆指伸出来,放在凳子上比划着,想把前头那一截剁去。菜刀生锈了,一刀下去指头粗的棍子就嘎的一声断了。”
在传统乡土社会,“读书人”一直是地方上的文化和治理精英;而当乡土社会难以维系之际,“读?”又是离乡离土、出人头地的一条有效路径。然而《读书》中培养儿子忠福读书识字的父亲却一语道破:“字就是金子,银子”,“读书人”就是“读书过日子的人”。“肚里有货比田里仓里有货保险。肚里的货不怕天干,不怕水淹,不怕霜打,不怕虫吃;白日不怕人抢,黑夜不怕人偷;借又借不去,抢也抢不走;总是自己的,活着盛在肚子里,死了带到棺材里。肚子里有货,走遍天下都不怕。没吃的,拿出一点来就可换一大海碗干饭;没穿的,拿出一点来就可换一身新衣裳;肚子里还有,就再拿,就可换房子,换田地。只要肚子里货多,就可换好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玩的。缺什么换什么,想什么换什么,连俏婆娘都可一换一大篓子……”说到底,“读书”和“种庄稼”并无根本区别。然而,正如“种庄稼”要靠“天”吃饭;“读书”也要靠“天赋”吃饭。忠福的自然天赋实在有限,一场怪病之后就再也不愿读书,最终只识得一个“人”字。但他仍执拗地将这个字教给自己的儿子,仍希望儿子有朝一日成为“读书过日子的人”。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在蔡铮笔下,吃喝、生育、家庭关系、读书教育等等传统乡土社会最为基本的方方面面,其底子里都时刻潜伏着灾荒、疾病、残缺、颓败、荒诞、无常……蔡铮本人生于湖北红安的贫穷农家,虽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攻读历史学硕士和社会学博士,但始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对乡土的呈显不是要以现代“批评”传统、以城市“回看”乡村、以人性“反思”礼教、以文明“启蒙”野蛮,而是以乡土人的内在视角展示出:即使乡土社会的种种价值逻辑本身是可欲的,在真实的乡土经验中它仍难以持久维系下去。乡土生活以“自然”为基础。但“自然”本身从来不只是“天人和谐”、“田园风光”,基于“自然”的生产生活本就极不稳定甚至危机潜伏。蔡铮试图通过这些故事不断逼问:对于从“自然”里长出来的乡土人来说,如果他无法顺利地春耕秋种、生儿育女、孝悌恩爱、光宗耀祖……如果他无法将自己的生存安放在乡土社会绵延悠长的意义链条中,又该怎么办?
从更深层面来看,“自然”本身的不确定甚至荒谬性对乡土社会的“天理”正当性直接构成了挑战。《种子》中,好人盛福无法再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他所遭受的“天谴”显然与其曾经犯下的小小过错极不相称。《天德》中在军队当兵的天德仅仅因为妻子拒绝床笫之欢就任由自己的性情杀掉对方,他对自己的盲目的性情几乎全然浑不自知。在《流氓》中,一个外乡人因被误解为耍流氓而被人打倒,接着全村的人都过来不由分说地对他拳打脚踢。作者从几个施暴人的视角分别展开叙述:他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积蓄了太多窝囊、愤懑和怨恨,都急需一个施展暴力发泄情绪的对象,而那个无辜的外乡人恰好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成为这个对象,至于他是否真的有流氓行为根本不重要。在貌似“天人合一”的乡村图景中,“天”所自然生予的血气、欲望、愤恨、嫉妒、暴戾蔓生滋长,而“天理”、“老天爷”本身却无力在义理上有所回应。近现代的知识人、革命人曾试图寻找一种取“天理”而代之的价值逻辑,在《天德》中:杀妻的天德向既是好友又是上级的韩道自首,因为天德救过自己的命,韩道非常不想杀他,但想到杀人偿命“是纪律,也是天理”,只能忍痛对他执行死刑。然而行刑的人们也觉得天德是出于情绪失控才杀人,罪不当死,就在射枪时故意偏离而保他一命。“死”而复“生”的天德本想好好活着,但按照“纪律”,却不得不在上级要求下被第二次执行死刑。小说从韩道的视角展开叙述:貌似公正无私的“纪律”虽然无比“正确”,却完全外在于自己(韩道)和自己所属群体的一般情感体验,这种孤零零的“道理”变得没有“意义”。
在他笔下,即使没有“外部”的价值参照,乡土社会的凋敝、颓落、失序、失范仍就不可挽回,它不再可能成为任何一种怀乡情绪的寄托。
三
在现代早期乡土文学中,“逃离”与“返回”几乎形成一个颇为常见的“对生”结构,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尤为明显。首先,“返回”的“我”(第一人称叙述者)虽曾生长于这片“乡土”,却早已游离、漂泊于“乡土”之外;这使得“我”总是以“城市人”、“现代人”、“启蒙者”、“见证者”的“外部”视角对“乡土”加以观照。同时,乡土社会的困境几近于一个封闭的死循环,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干预,它依靠自身很难产生出自我疗救的力量。第二,与“逃离”-“返回”结构相伴生的则是两个维度的交织:“记忆-抒情-家园”-“现实-批判-荒野”。⑥其中任何一维都很难说是乡土人自己的真实经验,而更多地传达着作为现代知识人的“我”所具有的生存意续。在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这一脉乡土文学的书写进路中,早期乡土文学中的现实批判向度进一步被弱化,诗意抒情向度则几乎被发展到极端。相对而言,蔡铮的笔调冷静、克制、简洁,甚少抒情色彩,几乎没有议论。这是在从传统乡土文学汲取养料的同时,对那种现代知识人“怀乡病”情绪的自觉摒弃。剥离掉抒情色彩的“乡土”不再是归宿和家园,而是出走和告别之地,是生命发育必须斩断的脐带,是精神成长所要逃离的母体和父权。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逃离”的动力不在于对任何一种已然明确的价值类型、生活理想的向往,而在于急于摆脱自己被抛于斯所命定的苦难。《老师》着力写了和清、世忠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父亲告诉和清:“只供他读完高中,考不起就回来放大卵子牛;湾里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没人中过秀才,没人上过大学,湾里就看他能不能把祖坟扒动。”为了死活不再“回去放大卵子牛”,两个孩子偷了家里要卖钱的花生,一路背到县城中学去请教水平更高的冯老师。后来考上大学、做了外交官的和清常常想:“没遇上冯老师他会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早被枪毙了吧?”《走》同样讲了一个通过读书“逃离”乡土的故事:主人公为民的故乡满是霸凌盗娼,他自己的原生家庭更是阴影重重(贫穷、压抑、父亲的控制、弟弟的欺负);通过高考复读,他终于离开了乡土“走”到县城、“走”到外省甚至“走”到美国,新途即使满是坎坷,也永不愿再回头。这正是“种子”意象的意蕴所在:它深埋泥土,虽饱受土壤的贫瘠、石砾的挤压、日光的曝晒、风雨的摧打,但它的生命力终究使之可以破“土”离“地”,向着天空和日月伸展枝叶。《种子》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段落:在满是坟茔和鬼影的乡村,人与动物一样具有生命力,猪死了,只要“沾下泥土”就会活;人死了,只要“沾下泥土”也会活。乡土人的劲道、皮实、强韧,使得他们具有自我断奶、自我否定、出走和更新的可能。?是乡土叙事中与“寻根”“返乡”截然不同的另一维度。
回到当下,在笔者看来,蔡铮的乡土叙事有两层意义。第一,《种子》对真实乡土经验特别是其内生创伤经验的呈现,是对早期乡土文学现实反思传统的回归。在减少浪漫想象、诗化抒情、启蒙投射的同时,如何激活和深化这一传统并与当下乡土经验进行对接,有待更多的思考和探索。第二,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仍在进行,城市生活经验极速生长扩张的同时,“乡土”作为一种心理-文化积淀仍将长期存续于我们的体验结构深层。换言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乡土”因素与城市因素彼此相互交接、混合的心理-文化结构仍将继续存在;“乡土”经验作为“转型”进程中的个体创伤和群体创伤仍将潜在地在场。这些创伤经验既无“家”可返、无“土”可安,更不能简单化约为城市经验。作为不可见的“幽灵”,它们似乎只能在我们熟悉的经验模式突然断裂时涌现出来。就此而言,乡土文学或许不再是一个沉溺于怀乡病中的抒情主体的“投射物”,而是在“投射”活动失效时撞击我们的“陌异者”。
① ?继会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蔡铮(Zane Cai),男,1965年生于湖北红安县,1991-1994年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96-2000年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居美国芝加哥。代表作有:小说集《种子》,散文集《生命的走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③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2页。陈晓明:《革命与抚慰:现代性激进化中的农村叙事??重论五六十年代小说中的农村题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④ 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⑤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⑥ 刘忠:《“乡土中国”的经验怀想与文学书写》,《河北学刊》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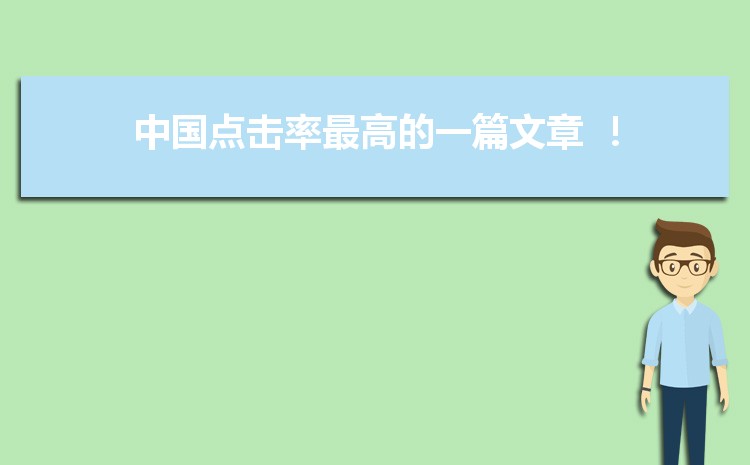 中国点击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2023-06-19 21:58:07
中国点击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2023-06-19 21:58: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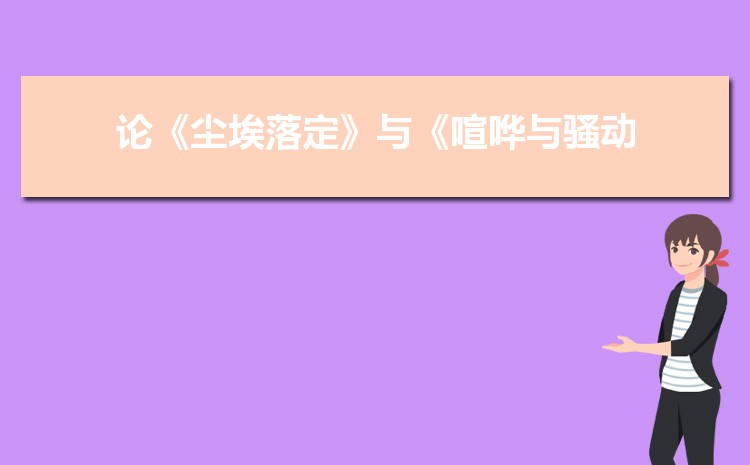 论《尘埃落定》与《喧哗与骚动》中的疯子式人物2023-06-09 22:19:53
论《尘埃落定》与《喧哗与骚动》中的疯子式人物2023-06-09 22:19:53  周勋初先生治学方法举隅2023-06-13 04:35:58
周勋初先生治学方法举隅2023-06-13 04:35:58  香港启思版《中国语文》初中教材写作训练的编排特点2023-06-17 02:44:33
香港启思版《中国语文》初中教材写作训练的编排特点2023-06-17 02:44:33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附历年最低分排名2024-01-23 21:03:34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附历年最低分排名2024-01-23 21:03:34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附历年最低分排名2024-01-23 21:00:39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附历年最低分排名2024-01-23 21:00:39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哪个好对比?附排名和最低分2024-01-23 20:57:48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哪个好对比?附排名和最低分2024-01-23 20:57:48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现代物流管理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附历年最低分排名2024-01-23 20:55:04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现代物流管理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附历年最低分排名2024-01-23 20:55:0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附历年最低分排名2024-01-23 20:52:10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附历年最低分排名2024-01-23 20:52:10  2024年广东高考物理排名255150名能上哪些大学(原创)2024-01-23 20:49:20
2024年广东高考物理排名255150名能上哪些大学(原创)2024-01-23 20:49:20  合肥经济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附历年最低分排名2024-01-23 20:47:06
合肥经济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附历年最低分排名2024-01-23 20:4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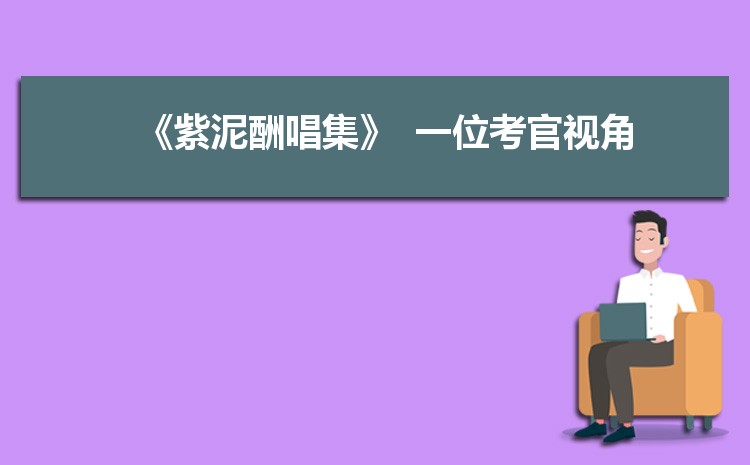 《紫泥酬唱集》 一位考官视角下的清代乡试2023-06-13 21:38:27
《紫泥酬唱集》 一位考官视角下的清代乡试2023-06-13 21:38:27  异域风光恰如故,一销魂处一篇诗2023-06-04 19:31:16
异域风光恰如故,一销魂处一篇诗2023-06-04 19:3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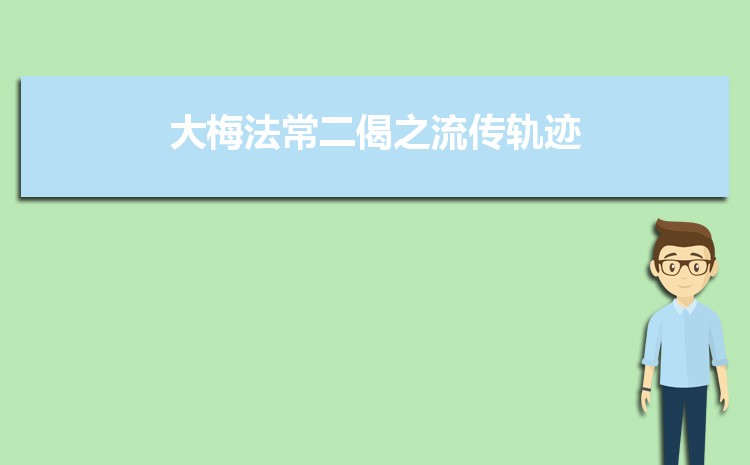 大梅法常二偈之流传轨迹2023-06-02 17:54:51
大梅法常二偈之流传轨迹2023-06-02 17:54:51